本文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9月13日在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办的“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”上的发言,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。

俞国林在会议现场发言
尊敬的寅彭先生、各位同道、主持人:
大家上午好!
非常荣幸能参与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办的“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研讨会”。忆及六月十三日,培军兄发来研讨会邀请函,询问我是否能够参会。对于这一议题,我抱有浓厚兴趣,当时便回复表示,只要届时没有上级安排的任务,定会拨冗出席。
如今身兼出版工作,要专门抽出完整时间深入思考并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字,实属不易!——但即便如此,为了本次会议,我还是凭借多年陆续收集的资料,计划梳理清华国学院导师与助教合影中的一些细节。
八月二十九日,我通过微信向培军兄询问会议议程。九月七日,培军兄告知,安排我在开幕式上“致辞”,并评议一篇会议文章。由于当时正忙于审定两篇汇报文稿,同时还要整理四篇本月中下旬需汇报的会议材料,遂申请减免评议工作,幸得应允。之所以这样安排,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层原因:
从议程设置来看:本次会议未安排校方、院方、系方领导出席讲话,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交流活动。寅彭先生代表高校,我则忝为媒体出版界代表,在三个半天的时间里,围绕二十四篇文章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,学术情谊与个人友谊相互交融。这是第一层原因。
从参会人员构成来看:共有三十一位参会者,其中二十位来自高校,一位为图书馆研究员,十位来自媒体出版行业,非高校人员占比超过三分之一。这种由高校组织、却有如此高比例非高校人员参与的学术研讨会,实属罕见。学术研究成果最终需通过媒体出版得以传播,而从事媒体出版的人员也更需要深入高校学者的研究领域,双方可谓优势互补。换言之,在当今的媒体出版界,同样活跃着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。这是第二层原因。
从会议主题设置来看:首先,“近三百年”是一个时间概念,它将中国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世纪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历史时期视为一个独立单元。这一概念虽非梁启超首创(王钟麒曾于一九〇六年在《申报》连载《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》,相关考证可参见李文昌、林存阳《“近三百年”历史叙事: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》),但确实是经梁启超使用后才固定为一个“专有名词”。在此简要梳理几个关键时间节点:①梁启超于一九〇四年刊出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第八、九章,内容“起明亡以迄今日”,标题为《近世之学术》;②一九二〇年他撰写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此后又陆续发表《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》《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》《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》《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》等文;③一九二二年申报馆为纪念创刊五十周年推出“最近五十年”系列,梁启超撰写了《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》;④一九二二年秋冬,他在东南大学讲授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;⑤一九二三年暑期,于南开学校讲授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》;⑥同年九月,在清华学校讲授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在《概略》的开篇,梁启超明确了“近三百年”的特定所指:
晚明的二十多年,已经开清学的先河;民国的十来年,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。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,似还适当,所以定名为《近三百年学术概略》。
梁启超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进脉络出发,将“近三百年”作为一个历史“时代单位”,从多个维度对明清之际至其撰写该书时的学术思潮进行了全面剖析。此后,顾颉刚《近三百年思想史》(1928,授课讲义)、沙孟海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(1930)、蒋维乔《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》(1932)、陈安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》(1934)、陈汝衡《近三百年中国民族思想之消长》(1934)、许造时《中国近三百年岁计表》(1936)、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(1937)、龙榆生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(1962)、来新夏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(1983)等众多学者,均相继沿用“近三百年”这一概念来命名自己的著作。因此,本次会议主题中的“近三百年”概念,亦是沿用此传统,而非以当下时间点上溯计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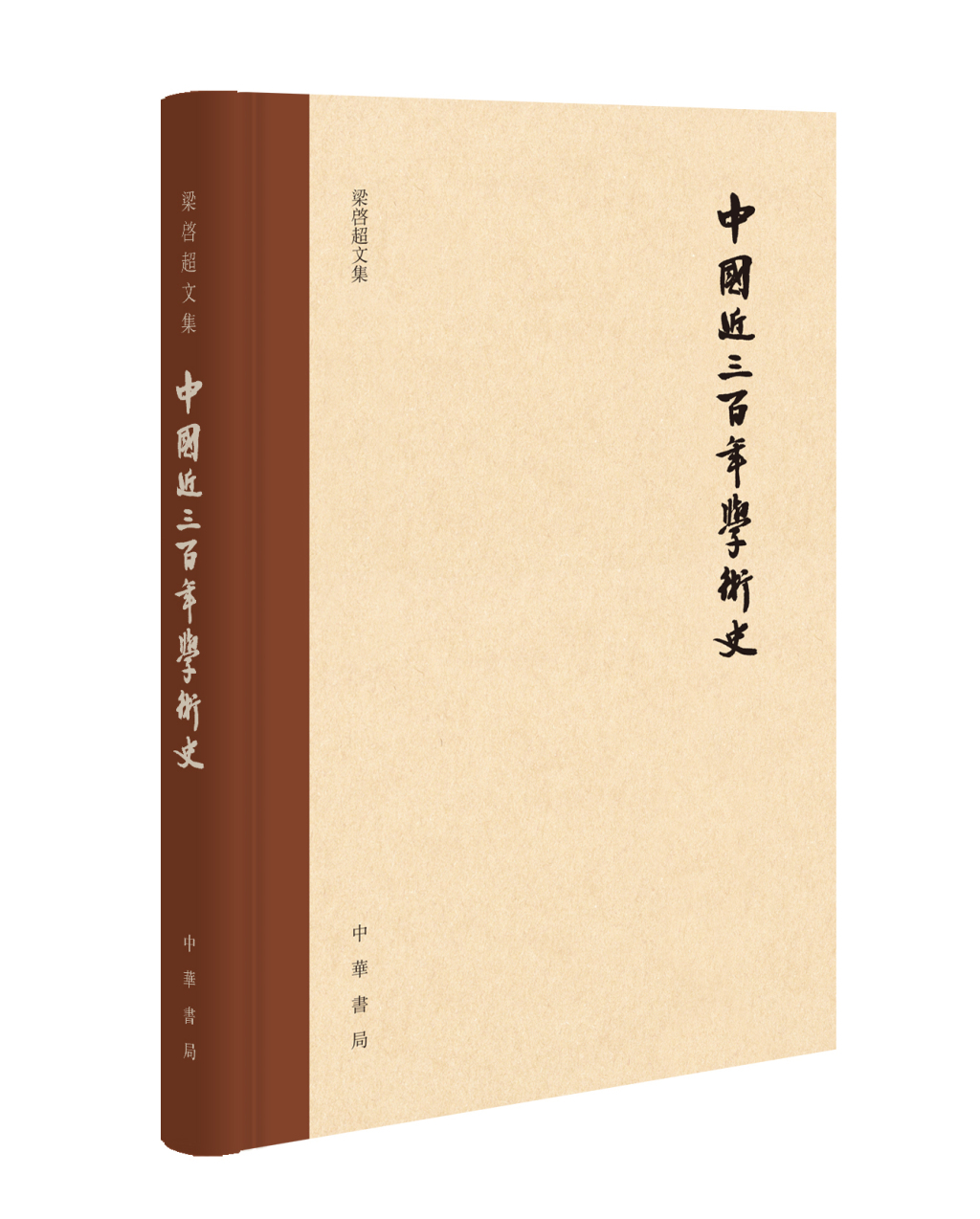
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
其次,“文学与文献”是本次研讨的核心范畴,其中“文献”更是基础所在。“近三百年”间,学术发展先是由对王学的反思转向乾嘉朴学,“考证学”因此兴盛;而后又因西学东渐引发思想启蒙,“今文学”随之兴起。我们站在今日的视角审视“近三百年”,与站在百年前回望这一时期,既有共通之处,也存在差异。
如今的学者,案头有移动硬盘,联网即可获取海量基础文献,鼠标一点便能唾手可得。与此同时,稿本珍本的不断发掘、日记书信的陆续公布,帮助我们发现了诸多以讹传讹的根源与流变,厘清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与脉络。例如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的“实证”与“冥证”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的“天地之故”与“人地之故”,以及书信中“夫君”与“家君”等用词差异,都曾引发相关论述。若非卢弼友朋书札专场拍卖的出现(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7迎春拍卖会“见字如面——卢弼友朋信札专场”),卢慎之的迂腐耿直、钱默存的诙谐调侃,又有谁能知晓呢?——当然,这也涉及到书信、日记等私密性文献的公布尺度问题。
今年是清华国学院成立一百周年。有一张广为流传的国学院导师合影,因不同的著录引发了三个问题:(一)中间站立者是陆维钊还是赵万里?此问题已得到解决(参见孟凡茂《陆维钊在清华国学院的任职时间考》、冯象《其志甚壮,其言甚哀》)。(二)拍摄的是全身照还是半身照?一九二六年《清华学报》刊登的是半身照,一九二七年《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》收录的则是全身照,可知二者源自同一底片。(三)具体拍摄时间?根据赵元任日记记载,可知拍摄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。我曾于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在朋友圈分享过相关发现,近来更是进一步细化了上述三个问题论述的文献依据。这便是第三层原因。——借此“致辞”机会,我将原本打算写成札记作为会议论文的结论,在此向各位宣读。

前排左起:李济、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,后排左起:章昭煌、赵万里、梁廷灿(1925年12月10日)
当今时代,文献资料层出不穷,可谓“河出图,洛出书”,甚至出现“想什么来什么”的丰富局面。因此,对于文献真伪的考辨至关重要,不可或缺。文献的校订与研究工作,哪怕只是校正一个字、一个句读,或是发现一种新版本、一部新著作,只要能够解决以往未知、未定的问题,或提供新的解读视角与观点,便是文献研究工作的最大意义所在。
梁启超曾言:“学术思想之在一国,犹人之有精神也,而政事、法律、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,则其形质也。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,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。”通观梁启超的相关论述,他热衷于探讨学术思想的“变迁”“蜕变”以及“变迁蜕变”的过程。
梁启超从清末步入民国,其人生经历中,政治与学术的相互影响,与清初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,因此他也常提及“清初五大师”(顾亭林、黄梨洲、王船山、颜习斋、朱舜水)。他说:
这五位大师所处的时代情形,的确有许多和现代相同的地方。他们都是生于乱世,自己造成一派学说,想来引导当世的人。那末,就很像现在的中国,一方面国事紊乱到极点,一方面有一般人讲这个主义,谈那个学说,都是“异代同符”的。
这种“异代同符”的经历,使得梁启超在叙述前一段历史时,采用了“近三百年”这样一个“时代”概念,从而跳出了传统“断代”表述的局限。审视历史发展,既要追溯其“源”,更要了解其“流”,这正是追求学术思想的核心所在。
尽管学术风尚会随时代变迁,但学术服务于当代的精神,在历史叙事中洞察当下、服务现实,以及文献研究“以复古为解放”的目标,即贯通古今、经世致用,是我们应当始终坚守的。这种以文献为基础的坚持,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,有九分材料不说十分话。梁启超在论述研究者应秉持的态度时强调:“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,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,致读者起幻蔽”(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第三章《研究法及本书研究之范围》)。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成立二十余年,致力于编纂、校订“近三百年”以来的重要文学文献,引领并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,正如顾颉刚所言,是以“求真的精神,客观的态度,丰富的史料,博洽的论辩”来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。
预祝“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”取得圆满成功。
谢谢大家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