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是否真正洞悉内心的渴望?在模仿与竞争并存的当代社会,人性是如何被无形之手雕琢的?
法国杰出人类学家、法兰西学院院士勒内·基拉尔的首部访谈合集《欲望的先知》汇聚了跨越二十余年的深度对话,深入探讨“模仿欲望”“替罪羊机制”“暴力与神圣”等核心命题,堪称其学术生涯的思想精粹。
基拉尔被尊为“人文学科的达尔文”,其理论对库切、昆德拉等文学大师影响深远。在这部访谈中,他以诙谐犀利的话语,剖析了从莎士比亚著作到“9·11”事件、从网络消费风潮到身材焦虑、从美国政治生态到家庭伦理等诸多现实议题。这不仅是一次思想梳理,更是对当下社会的深刻洞察。
9月20日晚,《欲望的先知》译者钱家音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陆远齐聚南京方所书店,引领读者深入基拉尔的思想宇宙,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宋思洋主持活动。这场文学、哲学与人类学的跨界对话,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自身欲望与现代生活的独特视角。以下为对谈内容的文字整理。

对谈现场。从左至右依次为宋思洋、钱佳音、陆远
基拉尔是何方神圣?一位内敛而深刻的古典学者
宋思洋:对于现场不少读者而言,勒内·基拉尔或许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请陆老师简要介绍,基拉尔是谁?为何他被誉为“人文学科的达尔文”,在思想界享有崇高地位?
陆远:基拉尔在公众认知中的知名度或许不及同时代的福柯、布尔迪厄等人,但他在欧洲学术界的认可度却不容小觑,因其入选法兰西学院,这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。在我看来,他属于那种典型的古典法式学者。他年轻时赴美求学并留校任教,但早年在法国南部阿维尼翁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他的思想底色。那里是欧洲基督教历史重镇,14世纪曾是罗马教廷所在地。基拉尔的父亲曾任由教皇城堡改建的博物馆馆长,因此他成长于浓厚的历史与宗教氛围中,大学专攻中世纪文献。其著作大量援引基督教经典,与中国读者存在文化隔阂,这或是其大众知名度不高的原因之一。
但我觉得他有点像“内秀型”学者,表面研究古老课题,思想爆发力却极强。基拉尔在《欲望的先知》中写道:“所有真正的思想都具暴力性。”这种暴力是观念的冲击力,虽不似肉体暴力直观,却能让人为之献身。基拉尔正是如此,其思想的穿透力与这位古典学者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,正是这种反差给世界带来震撼。
宋思洋:钱家音老师是本书译者,也是将基拉尔思想引入中文世界的先驱。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感受到这种力量?有无受到启发或遇到挑战的时刻?
钱家音:翻译前我已领略其思想威力,故接手译事时既感惊喜又觉忐忑,担心难以驾驭这位思想巨匠的著作。我最初对其了解限于文学批评领域,如其首作《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》及南大社·守望者出版的《莎士比亚:欲望之火》。但拿到书稿后,发现其理论体系宏大,横跨文学、人类学、神学及社会议题。
翻译过程犹如开启一扇扇窗户,让我窥见基拉尔思想世界的多元侧面。他是一位坦诚的学者,在书中阐述自己如何从尼采、弗洛伊德、拉康等理论中发展出独到见解,甚至修正早期观点。他还分享个人经历如何影响其对欲望与人际关系的看法,呈现出一个鲜活立体的基拉尔。
模仿欲望:为何我们总渴望他人拥有之物?
宋思洋:基拉尔最著名的理论即“模仿欲望”。此词虽显学术,实则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。陆老师能否为我们解读何为“模仿性欲望”?
陆远:我先以日常例子说明。例如,儿时课堂上看老师板书,或许都曾幻想自己站在讲台授课的场景,甚至偷偷在黑板上涂鸦,模仿老师姿态。这即是基拉尔所指的模仿。
再如恋爱经历。何为谈恋爱?我们自然想到吃饭、看电影、牵手、送礼。但可曾思考,这些行为为何成为恋爱标配?常听情侣抱怨:“你看别人怎么谈恋爱!”这“别人”或来自社交平台。初次约会吃什么、何时送礼,皆有“标准流程”。
又如,女孩想扮“坏女孩”,或会选择纹身、抽烟、泡夜店,谁告诉她这些代表“坏”?据基拉尔理论,这些行为模式非内心自发,而是模仿他人所致。所有物质与精神愿望,皆非源于真我,而是社会模仿的结果。当然,模仿研究非基拉尔首创,黑格尔、莎士比亚等均有涉猎。但其颠覆性在于,将模仿从儿童社会化扩展至全人类行为,乃至整个社会,视其为行动的根本动力。
他将欲望分为“外在”与“内在”。“外在欲望”清晰可知,如想成为学者或商人,是显性目标。“内在欲望”则是隐性模仿,如群体中讨论热点话题,不参与则难融群体。“鸡娃”“内卷”即典型“内在欲望”,整个社会陷入集体狂热,鲜有人能置身事外。
基拉尔理论另一重要颠覆是挑战马斯洛需求层次论,认为除基本生理需求外,人类欲望无固定层次。这可解释为何有人省吃俭用买奢侈品——非为“自我实现”,而是被潮流裹挟,盲目跟风。此潮流无序,明日流行何物未知。
宋思洋:陆老师以生活实例阐释“模仿欲望”,其实该理论最初源于文学文本分析。访谈中基拉尔自称通过解读塞万提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提炼理论,成就其代表作《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》。钱老师能否从文学角度进一步剖析“模仿欲望”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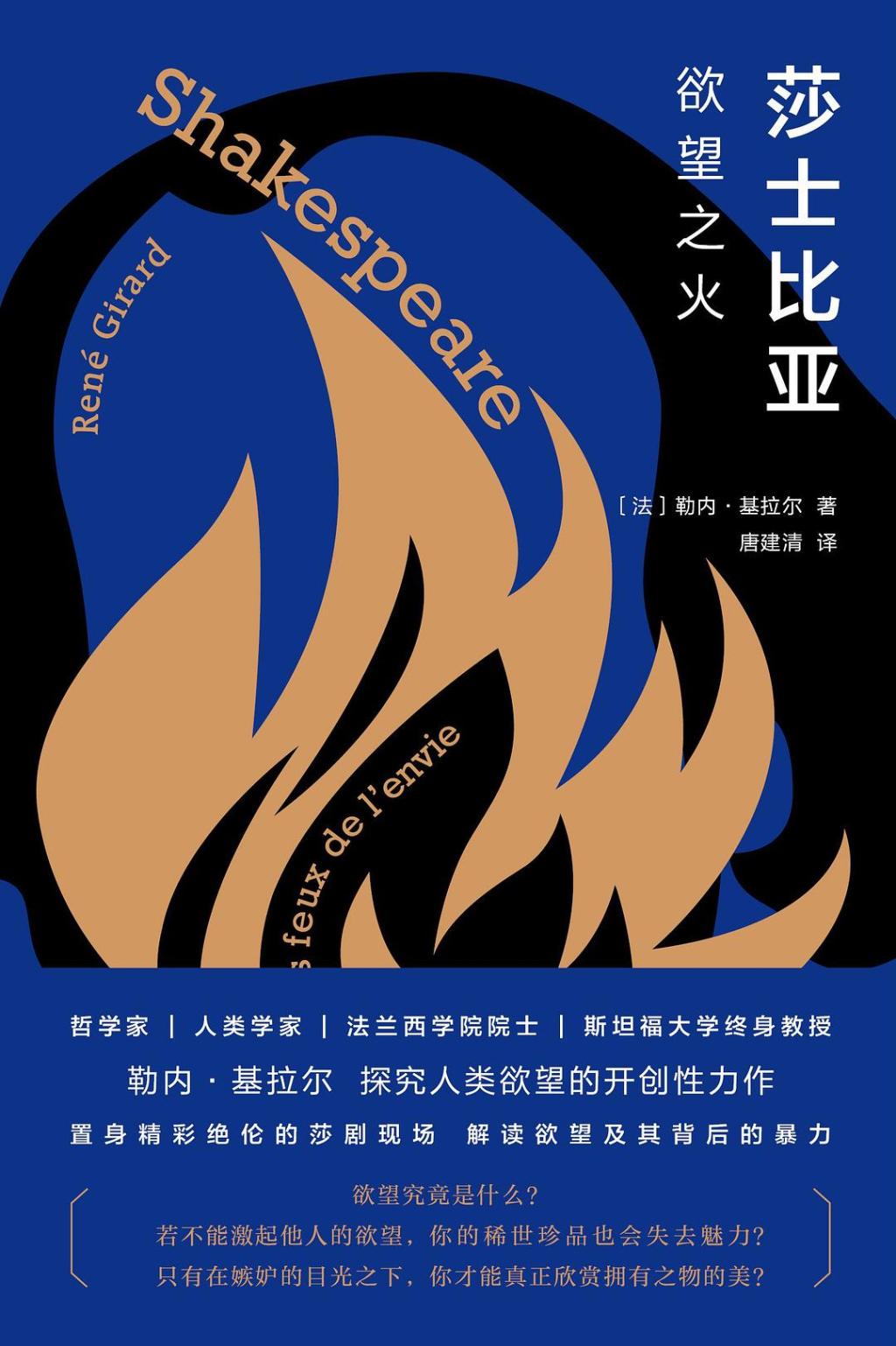
钱家音:是的,基拉尔首作《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》通过分析塞万提斯、普鲁斯特、司汤达等作品得出结论:伟大作家皆意识到“模仿欲望”的存在。他认为,主体对客体的欲望非直线关系,而是三角结构,必有“介体”介入。典型如堂吉诃德,其骑士执念完全模仿自小说人物阿玛迪斯,此形象即其“介体”。
在《莎士比亚:欲望之火》中,基拉尔解析莎士比亚作品。如《维洛那二绅士》,主角普洛丢斯原爱朱利娅,鄙视野心事业的友人凡伦丁。但当凡伦丁热恋西尔维娅并盛赞其“天仙”时,普洛丢斯突然移情别恋。读基拉尔前,觉此情节突兀。但用“模仿欲望”理论便易解:其欲望转向实为友人——“介体”——所激发,友人之欲成其之欲。
替罪羊机制:社会如何借献祭实现和谐?
宋思洋:我们探讨了“模仿欲望”,它易引发嫉妒、冲突与暴力。基拉尔由此衍生“替罪羊机制”。陆老师能否解释此机制运作原理?为何基拉尔视其为社会秩序形成关键?
陆远:简言之,当众人争夺有限资源时,冲突难免。极端解决方式是战争或决斗,但代价高昂。故人类社会演化出一法:不互斗,而找第三方无辜者,归咎所有矛盾罪责。此人即“替罪羊”。
此机制意义不在替罪羊是否真罪,而在其宣泄集体暴力,成为“安全阀”。一旦众认其罪,他便成选定罪人。有趣的是,被献祭者事后或神化,因他“牺牲自我,拯救群体”。基拉尔理论中,耶稣即此类形象,先为受难罪人,后成救世主。
从社会学看,任何社会存冲突,“替罪羊机制”正通过牺牲少数维持整体和谐。无此机制,社会或陷大规模内战。
宋思洋:在基拉尔的“替罪羊机制”中,社群借献祭替罪羊达和解,但人类真和解可能否?他对人类摆脱暴力循环持乐观或悲观态度?
钱家音:我认为他相对悲观。此需回溯其神学背景,他认为古神话掩盖替罪羊真相,使机制有效。但《圣经》从被迫害者视角叙事,揭示机制真相。此揭示带来可怕后果:当众知此为谎言、替罪羊无辜时,宣泄机制效力大减,难再平息社会怒火。
陆远:我前述带价值判断,觉替罪羊无辜受害,但从社会发展看,此机制是维系社会运行之必然。基拉尔与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共陷困境:他们诊断现代性问题深刻,却无解药。海德格尔言:“唯神能救我们。”这或是时代宿命——不可逃避性。那我们如何自处?借许倬云先生书名《往里走,安顿自己》。我们改不了时代与人类困境,但可充实内心。
基拉尔提出“模仿欲望”着眼点之一是人难觅自我。自我为何?唯在与人比较中得。今之最大问题,因互联网而较史上任何时刻更易失自我。如,展示孤独需发朋友圈,看有无点赞。我们须借告人“我孤独”以确认孤独。我们愈赖他人评价构建自我,此甚可怕。
我曾分享南大社版鲍曼作品《将熟悉变为陌生》《自我》,言:多一人读鲍曼就多一人得自由。基拉尔亦然,多一人读其书,或多一人知困境何在,未必能解,但多知一点,内心自由度增一分。
如何抵抗?在流量时代“向内走,安顿己心”
宋思洋:现聚焦现实,书中谈及“9·11”事件、美国党争、欧洲人口危机等基拉尔身边议题。今我们处社交媒体时代,追网红同款、为点赞焦虑、参与网暴……此等现象皆可用基拉尔理论解读。在被模仿欲望裹挟的当下,我们如何自处,寻出路?
陆远:切勿视互联网为一切。今有糟糕观点:万物与流量挂钩。常见视频评论区言:视频质优,何故流量低。此即陷现代性陷阱,何以高流量必与质挂钩?德导演赫尔佐格被问及是否在意流量时答:“你何以认为10万+重要?或10万+表10万倍愚蠢。”此言可作警示。我们固离不开流量,但不可万物与之挂钩。单一与迎合反引冲突,人因相似而争;尊重追求多元差异,反促和谐。
钱家音:我觉得陆老师所言不在意很重要。基拉尔在书中亦表反模仿态度,他曾拒人荐书,觉不能模仿,不为人意见奴隶。但后他发现,此顽固反模仿态为模仿病极端的表现。我们虽不应为人意见奴隶,但无法隔绝与他人一切。对积极模范的模仿不可避免,对创造力亦不可或缺。系统拒一切外模,临思想僵化之险。
陆远:若有立即可行之法,乃多培兴趣。法哲学家丹纳言:人每多一兴趣,抗外界社会能力增一分。此兴趣可极个人化,如好酒、集文具、甚至观蚁。只要你多一发自内心热爱,内心世界更充盈,焦虑便减。
我辈时代最大问题之一,是青年对什物提不起兴趣。只要非恶趣味,任何兴趣皆可在社会觅容身之所与同道。你来书店,非因小红书言此处出片,而是你真想来,来后不发朋友圈,内心亦悦,此方属你真获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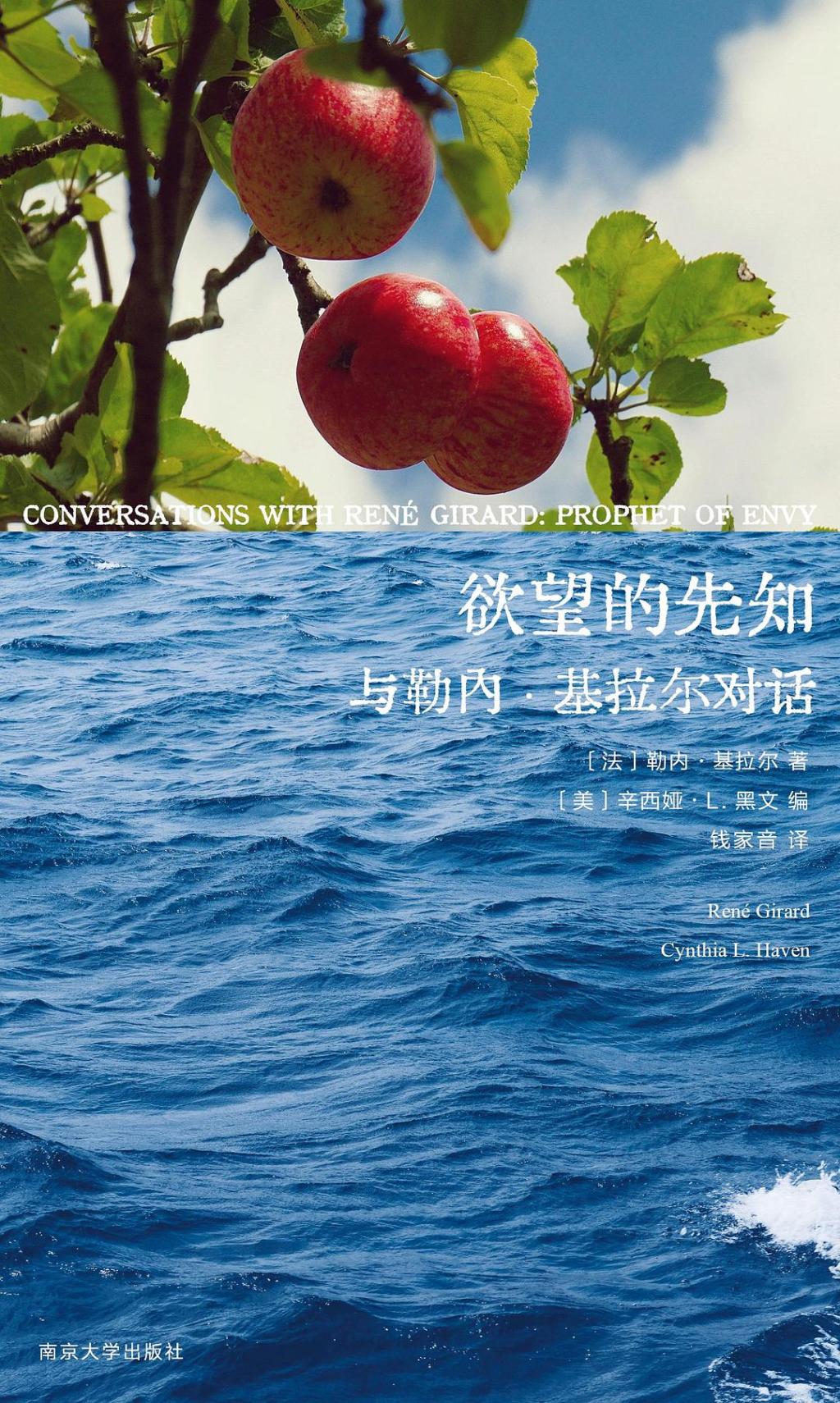
(根据2025年9月20日活动录音整理,内容有删节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