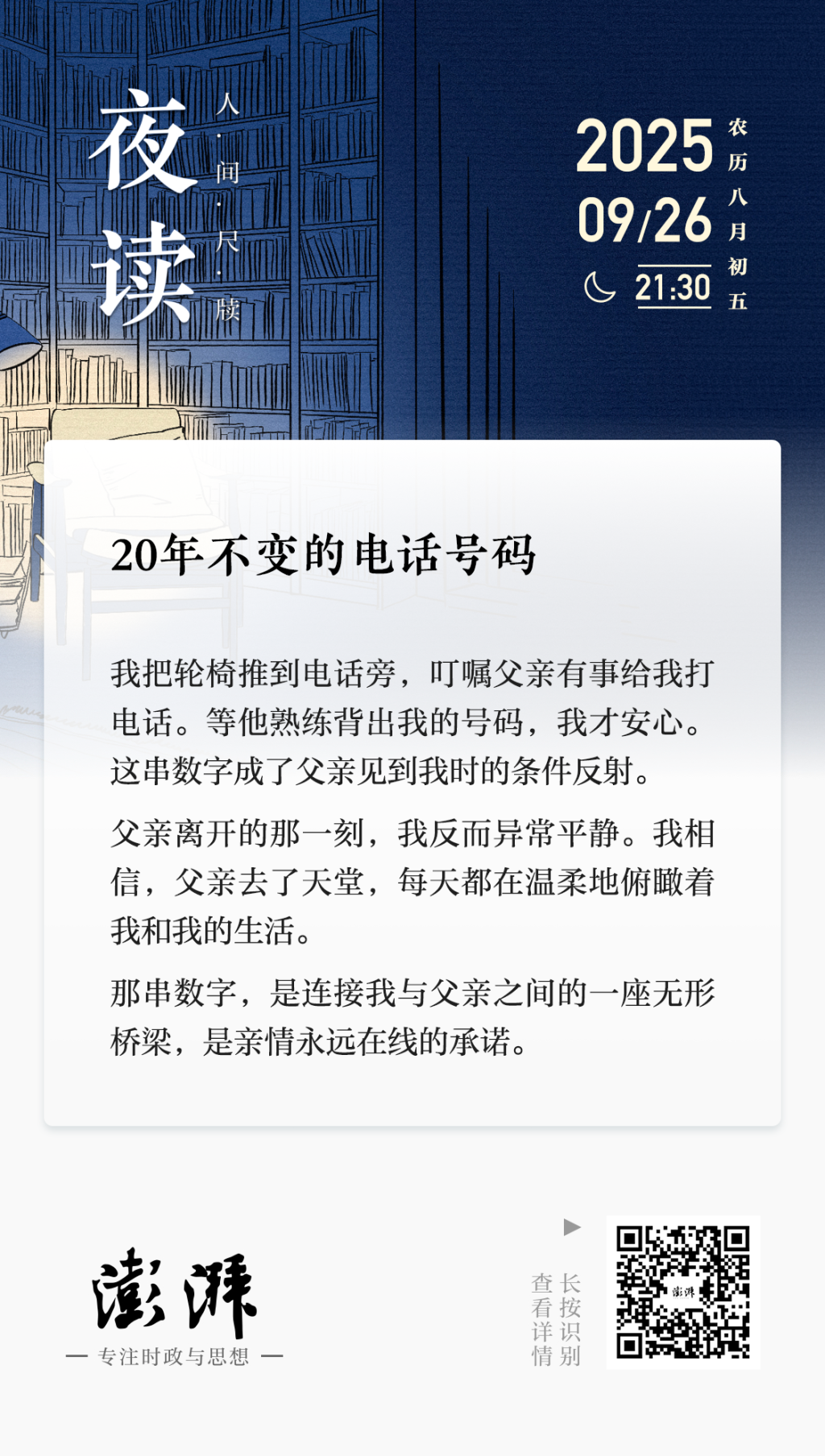2005年,对我们全家来说,是奔波于医院白色长廊的一年。
父亲的身体出现了状况。一开始只是轻微不适,我单纯地以为输液几天就能让他恢复成那个爱打扫院子的开朗老人。可随着住院频率增加,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——脑梗、血尿、行动困难。我和母亲成了各家医院的常客,办理住院流程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。
病情稳定时,我们也会在家中进行护理。偶尔母亲需要外出办事,我也得处理工作事务,留父亲独自在家总让人悬着心。每次出门前,我都会把轮椅推到电话旁,反复叮嘱有事一定要拨通我的号码。总要等到他一字不差地背出那串数字,我才能稍稍安心。日复一日,这组号码成了父亲见到我时的本能反应,仿佛只有完整背出这串数字,才能维系那份摇摇欲坠的安稳。
然而命运总是猝不及防。一个月后,"膀胱癌"的诊断书像惊雷般劈开了我们平静的生活。
我僵立在原地,泪水凝固在眼眶里,耳边只剩下血液奔涌的轰鸣。转身时,母亲早已泪如雨下,她颤抖的嗓音里,我仿佛听见整座生活堡垒崩塌的巨响。
由于错过最佳手术时机,父亲开始了漫长的放疗。我日夜守在他的病榻前。他总是强撑着精神劝我:"去工作吧,有急事我会打电话。"说着又条件反射般地背出我的号码。
我毅然请了长假,生怕错过与父亲相处的每分每秒,暗自祈祷奇迹降临。父亲的气色日益憔悴,偶尔清醒时见到我会勉强微笑,会催促我离开,会无意识地重复那串刻进骨髓的数字......他瘦得脱了形,皮肤泛着暗黄,连半个蛋黄都难以下咽。在病魔面前,我像困在岸边的旁观者,眼睁睁看着父亲在苦海里沉浮。
我甚至不敢轻易触碰他,生怕加重他的不适。除了疯狂咨询医生和偷偷抹泪,我竟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分担他的痛苦。
难得有不疼痛的时刻,这样的时光对我们而言堪比节日。我用轮椅推着他在医院花园晒太阳,甚至去附近的顺德市场散心,那时他嘴角会浮起浅浅的涟漪。
父亲真正离开时,我的心反而异常平静。我知道,他终于挣脱了病痛的枷锁,去往没有痛苦的天国。从今往后,他会在云巅之上,温柔注视着我的人生轨迹。
暖阳拂过面颊,像极父亲慈爱的目光。送葬的队伍缓缓行进在故乡的田埂上。秋收后的田野里,几株玉米秆在风中伫立,我独自望着它们环抱的新坟。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,已经去了我永远抵达不了的远方。
二十年光阴流转,通讯录里的名字来来去去,唯有这个号码始终未变。总有人建议我更换更实惠的套餐,我都微笑拒绝。因为我害怕,万一父亲需要我的时候,会拨不通这个号码。
这串数字早已超越简单的通信编码,它是我与父亲之间的心灵密语,是横跨生死的亲情鹊桥,是永不掉线的爱的承诺。
有些羁绊能够穿透时空壁垒,就像这个守护了二十年的电话号码。虽然电话那端再不会传来熟悉的声音,但真正的爱从来不需要信号传输——它早已化作血液里的潮汐,是无声却永恒的守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