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蒙古历史三大经典著作的核心,《元朝秘史》(蒙古文原称《忙豁仑·纽察·脱察安》)成书于13世纪中叶,是现存最早以畏兀蒙古文撰写的历史文献。这部兼具史学与文学价值的经典,详细记录了蒙古民族起源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、建立大蒙古国及窝阔台汗时期的军政伟业,尤其珍贵的是对成吉思汗早年颠沛经历、军事扩张策略及蒙古汗国制度建设的原生态记载。书中鲜活呈现了诃额仑太后、王罕、札木合等近百位历史人物的群像,其史料价值不仅覆盖蒙古早期政治、社会、语言研究,更被国际学术界视为中世纪欧亚史研究的关键文献。因元代列为"国朝秘典"严禁外传,蒙古文原典已佚,现存唯一完整版本为明代洪武年间译制的"汉译蒙音本",这也是"元朝秘史"名称的由来。
20世纪学术史上,蒙古学家札奇斯钦与史学大师姚从吾的合作研究尤为瞩目。二人耗时八年完成的《汉译蒙音元朝秘史新译并注释》,首创"蒙文还原-汉文重译"研究范式,结合元代典制、蒙古民俗及国际汉学成果进行系统注释,1978年出版后成为该领域里程碑著作。
札奇斯钦(1915-2009)作为现代蒙古学研究的集大成者,汉名于宝衡,祖籍内蒙古喀喇沁旗。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后,师从姚从吾专攻蒙古政治史,其学术生涯贯通中西方蒙古学研究体系,代表作涵盖《蒙古黄金史译注》《元代马政研究》等重要成果。
东方出版中心最新推出的《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》简体横排版,在保持原典风貌基础上,完成三项重要修订:系统性校勘旧版标点讹误与引文偏差,规范人名、地名等专有名词译写体例,优化蒙古文罗马字转写系统。本文原为姚从吾1958年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学术讲座的演讲实录,经札奇斯钦审定作为该书代序,此次经东方出版中心授权,由澎湃新闻独家首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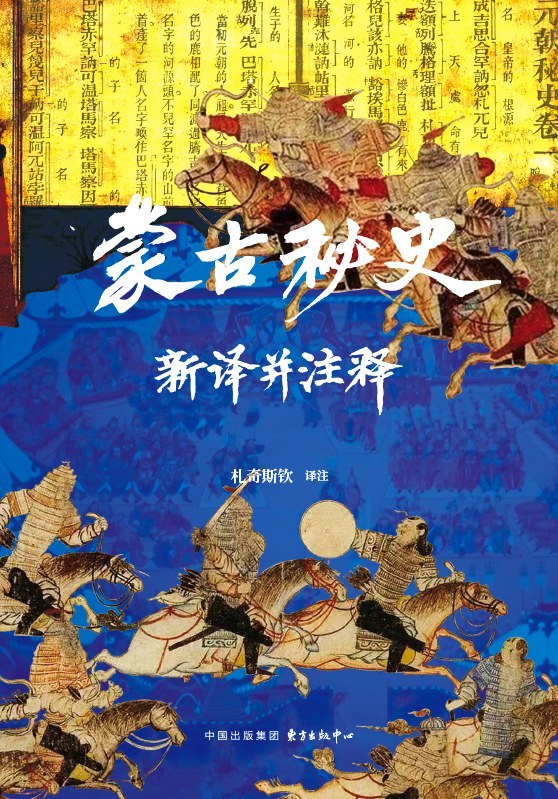
《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》简体横排版书影
一、引言
今天我们探讨的《元朝秘史》,堪称汉籍中的"史学奇珍"。这部著作不仅在文献形态上独树一帜,其蕴含的历史信息更对重构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历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作为专攻辽宋金元史的研究者,我将从文献特征、学术史脉络及国史定位三个维度,分享对这部经典的研究心得。
中国史学素有"断代深耕"的传统,北大史学系曾将国史划分为七大阶段系统整理。《元朝秘史》作为辽宋金元段的核心直接史料,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进入我的研究视野。留德期间,得益于与伯希和(Paul Pelliot)、海尼士(Erich Haenisch)等汉学家的学术交流,更深刻认识到此书的国际学术价值。1934年归国执教北大后,我与札奇斯钦先生共同开启对这部文献的系统研究,虽因战乱中断,然积累的史料与见解已渐成体系。
关于书名需特别说明:蒙古文原称"忙豁仑·纽察·脱察安"意为"蒙古机密史纲",即《元史》记载的《脱卜赤颜》(宫廷秘史)。现用"元朝秘史"之名源于明洪武译本,这一称谓既体现文献传承的历史脉络,也尊重明代学者的保存之功。值得注意的是,国际学术界多采用"蒙古秘史"称谓(如海尼士德文译本、伯希和法文注释本),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研究传统对文献属性的认知侧重。
二、《元朝秘史》的内容与性质
这部完成于1240年左右的文献,实为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两代帝王的"皇家实录"。全书十二卷二百八十二节,前十一卷详述成吉思汗(1162-1227)从蒙古乞颜部贵族后裔到欧亚征服者的一生,末卷记载窝阔台汗(1186-1241)继位后的军政举措。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将其译为《成吉思汗实录》,正是基于其鲜明的帝王传记特质。为便于研究,我将全书内容划分为十二个关键阶段:
(1)成吉思汗先世谱系(1-58节):追溯蒙古民族从巴塔赤罕到孛端察儿的二十二代传承,其中阿阑豁阿"折箭训子"等传说,较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多出十一代世系记载,具有珍贵的民族记忆保存价值。
(2)少年磨难时期(59-93节):记录铁木真十三岁丧父、部众离散、被泰亦赤乌部俘虏等关键经历,斡难河畔母子艰困生活的描写,展现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。
(3)联盟与分裂(94-119节):叙述与克烈部王汗、札答阑部札木合的"安答"(盟友)关系建立与破裂过程,反映蒙古高原政治势力的复杂博弈。
(4)本部崛起(120-140节):重点分析1189年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本部可汗的政治程序,此时尚未称"成吉思",学界对"成吉思"称号的确定时间仍存争议(我主张1206年建国时正式称汗说)。
(5)统一蒙古高原(141-149节):详述1201年阔亦田战役击溃札木合联盟,消灭泰亦赤乌部的军事过程,展现蒙古军事战术的早期发展。
(6)决战克烈部(150-188节):这部分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,生动记载与王汗的草原争霸战,其中"班朱尼河盟誓"等场景描写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。
(7)西征乃蛮与建国(189-201节):记录1204年征服乃蛮部、擒杀太阳汗的决定性战役,札木合的最终结局在此阶段交代。
(8)帝国制度建设(202-234节):1206年斡难河源忽里勒台大会的详细记录,包括九十五千户分封、怯薛军(护卫军)制度创立等立国根本制度。
(9)北境经略(235-246节):记载收服林木中百姓、处理萨满阔阔出专权事件,反映蒙古帝国对边疆民族的统治策略。
(10)欧亚征伐(247-264节):蒙古三次西征的原始记录,其中对花剌子模(撒儿塔兀勒)战争的记载可与《世界征服者史》相互印证。
(11)灭夏与逝世(265-268节):1227年成吉思汗临终部署与西夏灭亡的历史过程,关于其享年存在六十一岁与七十二岁两说(我持后者)。
(12)窝阔台汗时代(269-282节):记载1229年忽里勒台大会、灭金战役、长子西征及驿站制度创设等关键史事,末节窝阔台"自述四功四过"尤为珍贵。
从史源学角度审视,该书具有三大特质:其一,成书于蒙古帝国鼎盛期(1240年左右),大量采用口述史与宫廷档案,如孛端察儿征服兀良哈部的记载,保留了蒙古先民的历史记忆;其二,多采用对话体叙事,如成吉思汗与札木合"煮人肉"辩论等场景,具有当事人自述的鲜活质感;其三,制度记载详实,如怯薛军"四杰""四狗"的职务分工,弥补了《元史》职官志的记载空白。
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281节窝阔台汗的自我剖析:"平金、立站赤、凿井、设探马赤"四功与"沉湎于酒、强取斡赤斤部女、冤杀朵豁勒忽、围猎扰民"四过的自我批判,这种帝王自白在中国正史中极为罕见,堪称中世纪政治史研究的绝佳案例。
三、《元朝秘史》现存的版本与它在国内外研究的概况
现存《元朝秘史》主要有两大版本系统:十二卷本(汉字译音本)与十五卷本(汉文总译本)。前者保留蒙古文原音的汉字转写(如"成吉思"对应"cinggis"),后者仅有汉文译文,这两种版本构成国际研究的主要文献基础。
甲、《元朝秘史》现存版本
(一)叶德辉观古堂刻本(1908):这是十二卷本的首个活字印本,底本为文廷式影抄明洪武本,现藏陈垣励耘书屋。该本保留"汉字译音+旁注+总译"三体结构,海尼士德文译本、白鸟库吉罗马字转写本均以此为底本。虽存在卷八错简等瑕疵,但开创了现代《秘史》研究的文献基础。
(二)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(1936):涵芬楼藏顾广圻校抄本,纠正叶刻本多处错讹,其中四十一叶配补北平图书馆藏明初刊本残叶,文字更为精准。此本成为后来学术研究的权威版本,札奇斯钦新译本即以此为底本。
(三)永乐大典十五卷本:仅有汉文总译,分卷与十二卷本不同但节数一致。钱大昕藏本、李文田《元朝秘史注》均属此系统,虽便于阅读但丧失蒙古文语音信息,学术价值稍逊。
乙、我国学者对于《元朝秘史》的注释与研究
清代学者已开启《秘史》研究:李文田《元朝秘史注》(1896)首开系统注释先河,虽限于十五卷本,然征引《圣武亲征录》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等文献,具有开创意义;沈曾植《元秘史补注》(1945)首次考订蒙古文原名,并附"九十五功臣考",展现晚清西北史地学的研究水准。
现代学术史上,王国维《蒙古史料四种校注》首创"二重证据法"研究范式;陈垣《元秘史译音用字考》系统分析明代译音规律;陈寅恪先生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,揭示蒙古语与阿尔泰语系的亲属关系。这些研究共同构建了中国《秘史》研究的学术传统。
丙、国际东方学者对《元朝秘史》研究的概观
(一)法国汉学派:伯希和的六卷本注释(1949)以语言考订见长,纠正海尼士译本多处错误;田清波(Antoine Mostaert)《〈元朝秘史〉若干问题研究》(1950)对蒙古游牧制度的解读尤为精到。
(二)德国东方学派:海尼士1941年德文全译本虽存在季节日期误译等问题(如将"狗儿年秋"误译为"狗儿年春"),仍是欧洲首个全译本;鲍普(Nicholas Poppe)的蒙古语语法研究为文本解读提供语言学基础。
(三)日本东洋学派:那珂通世《成吉思汗实录》(1907)开创日本研究传统;白鸟库吉《音译蒙文元朝秘史》(1942)完成蒙古文原音的罗马字转写;小林高四郎《元朝秘史之研究》(1954)从文献学角度系统考证成书年代与版本源流,代表战后日本研究的最高水准。
(四)美国汉学派:洪业(William Hung)《元朝秘史流传考》(1951)梳理版本传承脉络;柯立夫(Francis Cleaves)正在进行的英译本,采用"逐字对译+学术注释"体例,预计将成为英语世界的权威版本。
俄国学者帕拉狄由斯(Peter Kafarov)1866年完成首个俄译本,郭增(Sergei Kozin)1941年出版的三卷本注释本,在蒙古语词汇研究方面具有特色。这些国际研究成果共同构成《秘史》研究的学术共同体。
四、《元朝秘史》在国史中应有的地位与对于它的新认识
甲、《元朝秘史》在国史中应有的地位
作为首部由少数民族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正史级文献,《元朝秘史》在中华史学中具有独特价值:其一,打破汉文文献的单一叙事视角,提供了游牧民族的自我历史认知;其二,其记载的草原游牧社会运作机制(如"斡耳朵"宫帐制度、"忽里勒台"议事传统),为研究北方民族政权模式提供了鲜活案例;其三,书中保留的蒙古语词汇(如"安答""怯薛")与社会组织名称,成为民族语言学研究的活化石。
乙、对于现存《元朝秘史》应有的新认识
在民族史研究层面,该书至少提供了七方面的新认知维度:
(一)政治组织演进:从"兀鲁思"(部落联盟)到"也客·忙豁勒·兀鲁思"(大蒙古国)的国家形态转型,可清晰观察早期国家形成的完整过程。
(二)军事制度创新:"千户制"的全民军事化管理、"怯薛"护卫军的层级结构,展现了游牧民族军事组织的独特智慧。
(三)经济生活记载:对斡难河流域游牧经济、狩猎活动与原始农业的描写,补充了北方民族经济史的研究空白。
(四)法律文化传统:"札撒"(法律)的形成过程与实施案例,反映蒙古社会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。
(五)社会关系网络:"安答"(义兄弟)、"那可儿"(伴当)等特殊人际关系的记载,揭示游牧社会的组织纽带。
(六)军事战术研究:第170节记载的"波浪式冲锋"战术与第171节的阵法部署,是中世纪军事史研究的珍贵实例。
(七)文化娱乐生活:那达慕大会、马头琴演奏等民俗活动的描写,保存了蒙古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。
随着《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》简体横排版的出版,这部经典文献将获得更广泛的学术关注。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,《元朝秘史》所蕴含的历史智慧与文化价值,必将为理解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提供新的学术视角,其作为"草原文明的史诗"的独特地位也将更加凸显。
